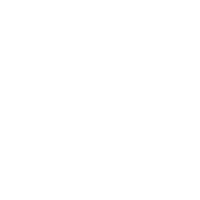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刘永加
死者是自缢身亡还是被人勒死后伪装成上吊,决定着案件的性质,也影响着办案的方向。而这其中最直接最关键的证据就是尸体上留下的绳痕。在古代各方面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法医”精心勘察,从案发现场找出那一根绳子留下的线索或破绽,从细节中还原真相……
无知仵作
耽误案情
根据相关记载,缢死的绳结大致有三种:一是活结,这种绳结一头打个固定的扣,另一头穿入这个扣,可以活动,古代称为“步步紧”; 二是死结,即绳套的大小固定不变; 三是缠绕,就是用绳索绕住头颈。
凡是自缢身死者,头颈上都会留有明显的“八字痕”。这是因为自缢者身子悬空,自身下垂的重量使绳索深深地嵌入舌骨与甲状软骨之间,颈的两侧受力多些,相对说绳索入肉也深些,颈后结节处,几乎就没有绳索的痕迹了,所以自缢者的颈部留下的绳索痕迹,就像一个“八”字。而被他人吊死的,虽然也可见“八”字,但绳痕往往不规则。
但也有些自缢的人可能并没有明显的八字痕,同时身体上还有别的伤痕,这就给判断真正死因带来了不少麻烦。
清代法医学著作《重刑补注洗冤录集证》 就记载了一个被尸体上的伤痕误导的案例。
清乾隆三十一年,湖南安仁县邓步青向官府报案,说他的妹妹曹邓氏被丈夫曹泽金打死。曹泽金则供称,邓氏是被他斥责后自己吊死的。
仵作检验尸体后报告显示,邓氏咽喉没有致命的吊死痕迹,左胸有被棒打留下的伤痕,脑后有木器的伤痕,左后肋有棒伤,应该是被打死的。在这之后,曹泽金迫于压力一会供认妻子是被他打死的,但不久又推翻供词。案子始终没有定论。
因为案情反复,后任县令和另一仵作一起对尸体进行复验,他们发现邓氏的上下牙齿,左右手腕骨、十指尖骨都呈红色。县令和仵作根据相关记载分析,尸体牙齿变红,是由于缢死者的颈静脉压闭,而颈部的颈动脉和推动脉压闭不全,引起头部血管高度充血,出现瘀血,血液流进齿髓或红细胞渗入牙质小管所致。
至于邓氏的两手腕骨及十指尖骨出现红色,可能是因缢后悬空,血液堕积于上下肢,造成上下肢瘀血,渗入腕骨和十指尖骨的原因。这无疑都是因为邓氏自缢而留下的瘀血。
至于邓氏左右耳根的八字痕不明显,这是因为邓氏用的是阔布自缢,所以没有留下绳痕。
此外,邓氏的左臂肘骨有一伤青紫色,斜长一寸三分,宽三分; 左右肋有一伤青紫色,斜长一寸,宽三分,均是木器伤,并不致命。因此县令认定,邓氏是被曹泽金殴打后自己上吊身亡的。
那么原来的仵作为何会作出邓氏是被打死的结论呢?仵作解释,当时邓氏左胸和脑后的伤痕已经变了颜色,他就误认为这是致命伤,由此上报。这个仵作缺乏经验,做出了错误结论,而原县令又不亲赴现场验看,全凭仵作的报告草草结案,这才让案件反复和拖延。
案情大白后,巡抚向皇上奏请弹劾了前任县令。
被殴致死
伪装自缢
《重刑补注洗冤录集证》 还记载了一则打死人后伪装成上吊的案件。
有一名杨姓女死者被发现上吊死于家中,根据她丈夫唐大拔的说法,他们家有两间铺屋,左边是客堂,右边是间店房,两屋间有一木梯。
官府到达时,死者的尸体已被解下,颈上缚有一条丝带,打成死结。据唐大拔说,死者是吊在木梯最上面的,脚下也没有垫踏的东西。
这个情况让办案人员很不解,他们从死者身上解下丝带,在发现尸体的地方丈量推演,尝试还原现场。结果他们发现,不垫踏任何东西就想将丝带挂到木梯上的横木,还要将自己吊起来,这不可能实现。而且死者上吊用的丝带打成了死结,办案者认为这也是不可能的,一个呼吸都困难的人怎么可能打死结呢?因此推测死者不是自己上吊。
调查现场之后,再检验尸体。办案者发现,死者脸部的颜色已经稍有变化。死者两眼睁着,嘴巴紧闭,舌头未伸出。咽喉上有一道浅淡的伤痕,推测是丝带留下的伤痕。左脸有伤,连到耳轮。死者的左手五指甲缝呈青黑色,右腿内侧有抓伤一处,长九分,宽四分,呈红色,但这些都不致命。反倒是死者耳根有一处伤,呈紫红色,像是手掌打的。办案人员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致命伤。虽然一般而言,掌伤不会致死,但有时打在要害处也会产生严重后果。耳根是较薄弱的地方,被掌伤后,可引起严重的脑震荡。死者可能就是因硬脑膜下积液或脑挫伤,而导致死亡。
排除了自己上吊的可能,又验明了致命伤痕,死者死后被伪装上吊的真相就确定无疑了。不过书中只着重记录了检验的情况,并没有明确记录凶手到底是谁。
辨析绳痕
洗清嫌疑
清代的许梿(1787—1862年),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海宁人,史称“吏事精敏,而日不废学”,典型的文人、学者型能吏。他“素留心检验尸伤损”,刊刻了《洗冤录详义》,这可不是简单的对宋慈原著的增注、解释,而是融入了许梿自己的多年实践经验,他还根据尸骨实物重新绘制了比较确切的全身骨骼解剖图。
《洗冤录详义》 中刊载了许梿在山东平度县做官时的一则案件。当时有人发现一名男子吊死在树上,但是没人认识这名男子。仵作验尸时,发现尸体的颈上有两道绳痕,一道紫红色,有瘀血; 一道红色,无瘀血。看样子是被人移到这棵树上的。
报案人对案件线索却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尸体从什么地方移来的。经过询问报案人,许梿得知这个村子共有十一户人家,除了一家父子二人赶集不在家,其他人都在。
于是许梿派人传来了父子二人,许梿一口咬定移动尸体的人就是他俩。父子两人害怕了,承认是他们动了尸体:“那天早上,我们开门看见一个人吊在门口,我们太害怕了,就把他移到离我们家远一点的一棵树上。”
许梿又问了死者当时的情况,父子二人称男子当时已经没有气了,只是两手还有些温热。
许梿于是分析,根据《洗冤集录》 的记录,尸体移动后的绳痕应该是白色的,而该尸却是红色,这一定是上吊不久,移动时血液还没有完全凝结的缘故。再从移尸的父子的供词中可以得知,他们见尸体悬在家门口,怕惹祸也觉得不吉利才将死者移挂到其他树上。
结合多方证据以及尸体所呈现的特征,许梿最终判定,父子俩不是凶手,男子确系自缢身亡。
《洗冤录详义》 还记载了一起5名女子同时死亡的案件。许梿在山东省任职时,检验自缢的案子不少,最罕见的是平度州白家5个丫头同时上吊一案。许梿得报后立即前往验看,只见两个丫头在同一条绳吊死,绳套一个是活结,另一个是死结。其余三个丫头同吊一条绳,一个是活结,两个没打结,只把绳子缠绕在颈项上。她们是怎样结扣的,怎样一块上吊的?看了之后,许梿一时摸不着头脑。这几名死者的伤痕没有异样,绳子的打结方式虽然怪异可也没有更多线索。
仅从绳子上是无法确定她们是自杀或是他杀的,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许梿从她们所穿的衣裳和所佩之物着手调查,看这几名死者穿的衣服,都极为华丽,而且各人身上都带有香囊荷包,似乎是真的做了一番准备才寻死的。
许梿继而审问了相关人证,都说这些死者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互相之间也没有矛盾。只有一个老太太说,这几名死者平时关系很好,常说“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这句话。而最近,白家的主人想把其中两个丫头嫁出去,导火线可能是这个。
许梿觉得这个老太太说的理由还算合情合理,结合相关证据,判断她们五人之死并非他杀,而是五人中有两人被主人“遣嫁”,她们不愿生离,才同赴黄泉。何况,多人同时被他人一同吊死而不留下任何痕迹是难以实现的,死者身上又无任何伤痕,只可能是自己所为。
许梿将案子详细汇报给上级官府。上级官府也对案件加以分析,又派官员一块审讯,都没有发现其他异常情况,于是就采纳了许梿的意见,稍作修改后结案。
蹊跷命案
令人唏嘘
晚清人吴炽昌在《客窗闲话》 里记载了一个乐亭县发生的奇案:当地有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赵杨氏,她的丈夫因长期做生意而出差,家庭也条件不错。只是夫妻俩没有孩子,赵杨氏在家寂寞,领养了姐姐的女儿银姑为养女,银姑也有十三岁了。
后来赵杨氏被丈夫传染了疾病,长期卧床不起,只好请了六十多岁的母亲杨王氏来作伴。赵杨氏丈夫的姨甥女张王氏有天前来探视,也在她家住了几天。
一天大早,平时一直给赵杨氏家送水的工人来送水,但喊不开门。到了晚上那工人又来,还是没有人开门。他觉得奇怪,就去请了邻里宗亲,大家把门卸下进入房内,结果看到赵杨氏等4人都已自缢身亡,而且方式还不同:赵杨氏将绳子系在高处窗棂上,自己拥着被子“坐缢于炕”。赵杨氏的母亲则把炕几竖起来靠着墙,在炕几的脚上绑了绳子,自己躺在炕上仰面自缢。张王氏与银姑则用一根绳子分头打结套住脖子,把绳子中间部分系在两人中间的柳木椅的椅档上,就像是个天平那样,两人在两端“坐地而死”。四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年轻的两个还涂粉画眉,头上簪花,脚上换鞋,好像要作客。
众人赶去报案,官府立即前来验尸,尸体上都没有伤,不是命案; 房里没有男人踪迹,也不是奸案; 家里一件财物都不少,更不是盗案; 死者从容妆饰,也不是吵架愤怒的样子。
四个人为什么要一同寻死?没有证人,无法查证原因。乐亭知县只好就以自杀结案。
可是赶回来的赵杨氏的丈夫,以及她的兄弟杨锷,都怀疑是有人暗害,见地方官含糊结案,就向上级官府申请再审。由于案情太过蹊跷,朝廷就命令由省按察使组织会审,将四具尸体解到省会再次检验。可是结论依然是自缢。
按察使只好推测四人的动机:赵杨氏因为病情医治无望而要轻生,母亲杨王氏是心疼女儿,养女银姑是要追随养母,张王氏是同情姨母,所以商量一起自缢。勘查现场上吊所用的绳子等也符合推测的实际,于是上报朝廷批准定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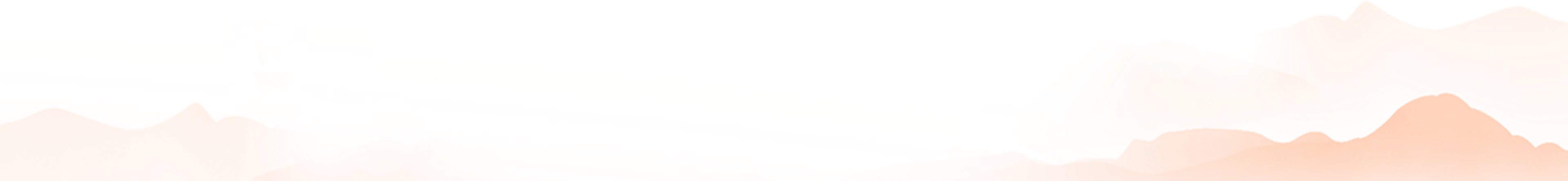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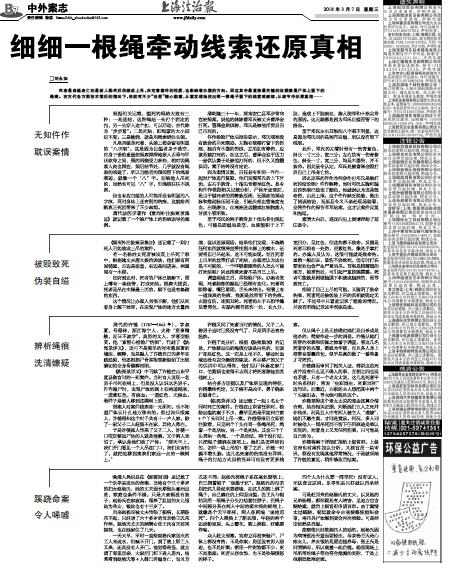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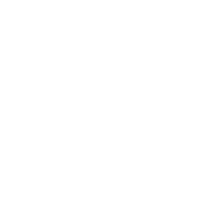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