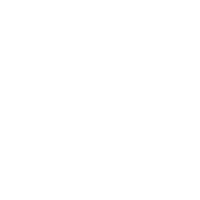网络成为了人们的基本生活平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正在逐步走向交叉融合,“双层社会正在逐步形成”。与此同时,网络技术的到来也冲击着原有的制度体系,越来越多的网络脱序行为、网络违法行为乃至网络犯罪行为涌现在日常生活中,网络犯罪正趋向于井喷式。在此背景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强大的网络社会结构性力量,其已不再是纯粹的商业活动经营者,还负有网络安全管理者的双重身份,俨然已成为刑事责任研究对象范畴。根据“两高”《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我们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指通过信息网络,为网络用户提供信息网络接入、通讯传输、网络缓存、网络储存、服务器托管、广告推广、支付结算或网络平台等中介服务的个人或组织。
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反思
近年来,“快播案”“深度链接案”等重大影响性案件引爆全社会的高度聚焦。
以“快播案”为例,法院认定快播公司构成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理由为快播公司拒不履行监管义务,放任淫秽视频在网上传播,构成了不作为的传播行为。而有学者认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的传播行为,应当看其是否履行了对淫秽作品的合理审查义务,要求快播公司逐条查看并删除其中的淫秽视频实为强人所难,因此难以认定快播公司构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正犯。也有学者认为快播公司同样难以认定为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帮助犯,因仅根据快播公司主动对用户上传的资源进行主动提取和缓存,难以证明快播公司与真正传播淫秽信息的犯罪行为人之间存在意思联络,而确定帮助犯至少需要有明确的认识。此种争议体现出网络帮助行为在实践中仍存在认定障碍。具体体现在:
第一,立法未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以类型化归责。
我国在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入罪时未明析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概念,虽在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中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了简单分类和服务类型的列明,但未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划分具体承担的责任,司法实践中呈现无法可依的状态。如快播公司主张其仅作为网络平台提供者,根据技术中立原则不对发布在平台上的淫秽信息承担责任,而法院对快播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详细分析,最终将其角色定位为网络视频软件提供者和网络视频内容管理者的角色,进而否定其行为的技术中立性、排除“避风港”原则的使用,而该类型认定仍因无立法的明确规制而饱受争议。
第二,客观归责主义理论存在疑问。
对于一般的P2P网络服务行为而言,其只为用户提供上传、下载软件的服务,仅仅是客观上对用户上传的侵权信息起到传播作用,而非内容提供商和管理者,对该行为是否以共犯理论要求其承担刑事责任在理论和实践中存有争议。而根据我国相关案例,基本都将此种行为以共犯理论入罪处理。而此种共犯理论已被德国、日本等学者批判,认为单方面的帮助行为不应以共犯论处。
第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安全管理义务边界不清晰。
我国并未具体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履行的具体管理义务,在此前提下,需承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刑事责任风险,有打击网络技术发展之嫌。就“快播案”而言,要求快播公司审查和过滤信息甚至到达某种程度,实际上并没有行业标准予以规定。从域外立法来看,大多否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审查信息的义务,且在判例中明确主管部门不得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植入信息内容的过滤系统,否则不仅会严重侵犯其经营自由,也会造成成本的高昂和复杂。
当前法律框架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模式分析
1.单独责任模式
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独立的犯罪主体地位,其实行行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完全取决于自身的主客观要素,本文称之为单独责任模式。具体包括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情形,作为情形下,为自己发布信息、修改他人信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转变为内容提供者,承担完全独立的刑事责任。在不作为情形下,存在行政程序前置——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此种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不同于直接实施电信诈骗等行为人,用户可以选择直接要求其作出删除等处理,也可以选择向有权的行政机关反映并要求处理,“用户反映—行政处理+责令不改—刑事责任”的模式既保障了用户的权益,也可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大的司法压力,防止刑法成为“一般性武器”。
2.共同责任模式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网络服务提供者可能作为帮助犯独立成罪,理论界称为帮助犯正犯化。因无论是共犯还是帮助犯正犯化,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认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人行为涉嫌犯罪事实的查清,故本文将其统称为“共同责任模式”。共犯模式与帮助犯正犯化模式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的区分主要体现在主观“明知”的证明标准不同,一方面“明知”的内容不同,另一方面是否可以适用推定方式及具体要求不同。共犯的“明知”不仅要求明知对方意欲实施犯罪行为,还要与对方有相应的意思联络。对帮助犯正犯化模式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明知”,我们认为其内容是存在对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具体的认识,并合理谨慎适用推定,具体应当遵循以下推定规则:其一,是否违背一般人的常识,即所谓的“被帮助者的明显犯罪性”,被帮助者显然是为了从事犯罪活动而寻求信息网络的技术支持,或者帮助者所提供的帮助显然不符合一般人的正常行为,如买卖“四件套”(银行卡、电话卡、U盾、身份证)的行为;其二,结合网络信息技术的特征进行合理的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明知只有结合上述特征才能给出较为合理的结论,主要应考量服务内容、服务对象的资质身份、服务手段、行业一般操作、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
3.模式竞合时的处理
上述单独责任模式与共同责任模式中的共犯模式和帮助犯正犯化模式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应遵循“单独责任——共犯帮助犯——帮助犯正犯化”的逻辑顺序进行认定。
第一,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本身参与网络信息的产生及实质修改等,其已超越服务提供者的身份,自行实施犯罪行为,是独立的责任主体,可独立构罪。
第二,在同时符合共犯模式和帮助犯正犯化模式的情况下,本文倾向于优先以共犯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是立法为了解决在下游犯罪行为人未到案的情况下不能追究帮助犯刑事责任的问题,实则共同犯罪更加能够还原案情的全貌,更能反映前因后果,在此种情况下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更加符合事实,并能够做到与主犯或者同案犯的罪刑相适应。同时,帮助犯本身是共同犯罪中的概念,将帮助犯正犯化是在打击犯罪的要求下,弱化非主要事实的查清诉求,以单独追求帮助犯的责任,也正因此法定刑设定得较轻。有学者指出这是出于“‘及时止损’的功利主义考虑”。因此,在查清全部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以共犯认定帮助犯的刑事责任更加合理。
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刑事责任体系的建议
(一)在刑事立法中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出入罪规范
1.完善司法解释,根据服务者类型分级划分刑事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既是提供网络服务业务的市场主体,也是对特定空间具有管理能力的监督管理主体。为了明晰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边界,有必要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不同技术服务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分类,设定与其类型和监管能力相匹配的审查义务,从而根据义务的履行情况,本文建议分为三类进行分级划分刑事责任。第一,网络接入服务是为用户建立连接互联网通道的中介服务,接入网络后,网络介入服务在技术层面无法编辑信息,也不能鉴别、控制网络中出现的信息,不再具有控制能力。因此难以要求提供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数据甄别、控制义务,只有在其事先知晓对方用于违法犯罪时具有拒绝接入义务和事中知晓后的停止服务、断开链接或报警义务。第二,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拥有固定的专业技术团队,对局部网络空间具有一定程度上事实性的控制能力,提供者应积极落实行业管控措施,自觉承担起与其技术特点所造成的法益侵害风险程度相当的注意义务,并鼓励利用技术主动建立效级更高的信息安全管理机制。提供者在接到监管部门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导致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等严重后果的,应承担刑事责任。第三,信息定位服务一般作为访问信息的中介,但若提供者明确了定位信息的内容,并使得用户通过定位直接打开了信息内容,而不显示信息原提供商,则应视为其将定位内容作为自己提供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传播行为,应要求提供此种深度信息定位的服务者承担保证信息合法的义务,进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2.规范行政前置措施,有效减少犯罪演化
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密切相关的刑法罪名之一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该罪是典型的前置程序型行政犯,以行政违法为前提,行政监管的有效规范能极大程度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违法从而递进演化为犯罪的可能。“行政责令”以及“改正措施”是行政程序前置的关键要素。“行政责令”侧重程序性规则,强调的是责令行为作出的方式;“改正措施”侧重实质性规则,强调的是义务改正行为作出后的实际效果。对于“行政责令”来说,应排除形式瑕疵的责令,而将书面的责令改正通知书作为必备的行政程序的形式和载体。对于“改正措施”来说,应排除抽象、简略、不符合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能力的“无效”措施,而避免强人所难。建议考虑赋予被监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一定的改正措施异议权,认为监管部门提出的改正措施确不可行的,有权向该监管部门提出复议。对于监管部门维持,网络服务提供者仍认为不合理的,监管部门应提交改正措施由第三方非营利性技术机构予以鉴定。
(二)在统筹企业自治与司法预防中打造多维治理体系
1.建立企业刑事合规体系,激励企业主动应对刑事风险
网络服务提供者越来越频繁地陷入违法犯罪的泥沼,而刑事处罚对于企业的打击往往是致命的,为了尽力避免那些有着技术能力、创新动力的网络服务企业的陨落,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刑事合规体系,主动应对刑事风险。具体而言,一是在实体法层面,建议在刑法条文中增设网络服务提供企业建立企业合规的刑事义务,将合规计划纳入企业刑事责任积极抗辩事由。综合考量犯罪类型、违法后果、犯罪形态等,对轻微犯罪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将已经制定并遵照执行有效合规计划作为出罪事由,不作为犯罪处理。对触犯重罪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将合规计划作为从宽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二是在程序法层面,将网络服务提供企业的合规计划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结合,进一步探索企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从犯罪治理层面丰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涵。三是在配套层面,建立检察机关对企业合规计划的动态监督评估体系,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在企业合规计划制定之时,对计划目的的正当性、设计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行监督,在合规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实时评估效果,及时纠偏、修正。
2.刑事处罚与非刑罚处罚措施并用,建立多层次惩罚方式
除刑事处罚之外,对轻微犯罪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更多考虑非刑罚处罚措施,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责令赔礼道歉、责令赔偿损失等。一方面,通过适用非刑罚处罚措施,以具结悔过的方式来完成刑事责任的追究,降低刑罚处罚对轻微违法网络服务企业的打击,避免小微网络服务企业因轻微违法而破裂,在惩处犯罪的同时更好地维护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强化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公开执行,在网络的加成作用下,网络危害行为往往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结果,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的危害行为会进一步波及社会上不特定大多数人的利益,也会降低民众对网络服务安全性的信心。采用公开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如通过媒体公开向社会道歉等,不仅使民众切实感受到刑法规制的力量,重拾信心,还可以对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起到警示、教育作用。
本文系国家检察官学院2020年度科研基金项目(编号GJY2020C01)研究成果。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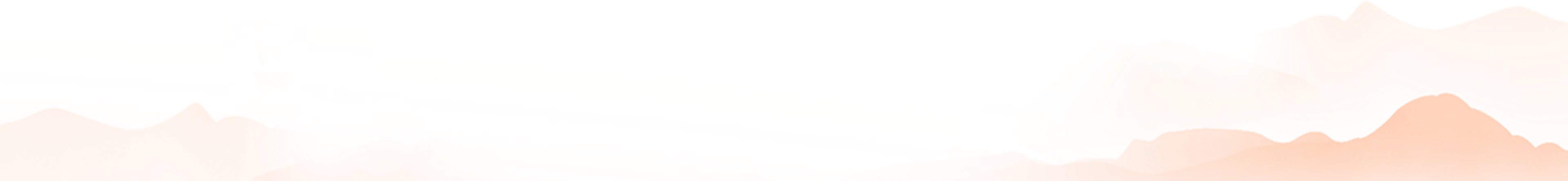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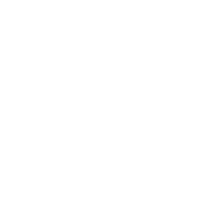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