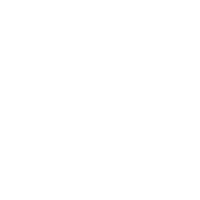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 孟高飞
依据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三十七条关于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更换和第一百四十六条关于违反法定任职资格的董事委任无效的规定,我国建立了以正式委任为基础的形式董事制度。2023年新《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七十八条保留了上述形式董事制度的规定,同时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第一百九十二条另设了由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组成的实质董事制度,由此我国建立了完整的董事制度体系。实质董事制度如何适用、如何与形式董事制度相衔接,成为理解与适用的重要问题。
适用实质董事制度需先厘清形式董事的义务责任体系
(一)形式董事的义务体系存在三层构架
新《公司法》对董事义务体系作了改造,建立起以守法义务为基础、以忠实勤勉义务为主干、以类型化的忠实勤勉义务为枝叶的多层级董事义务框架。从宏观的基础守法义务,到中观的忠实勤勉义务一般条款,再到微观的类型化忠实勤勉义务,三层义务体系逻辑严密、层次清晰。
第一层为守法义务。新《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这是董事的一般性、基础性义务,类似于法律的一般条款或基本原则,起到倡导、指引、补缺作用。此处的“法律”包括新《公司法》,亦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等法律。
第二层为忠实勤勉义务。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应当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和第二款“董事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明确了董事负有忠实勤勉义务以及义务的内涵和指向。此为忠实勤勉义务的一般条款,在无第三层类型化忠实勤勉义务条款可供适用时,可考虑适用该款规定。
第三层为类型化的忠实勤勉义务。以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第二款为基础,新《公司法》对忠实勤勉义务作了类型化列举,对原《公司法》的类型化列举作了改造和扩充。比如,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等均是对常见的忠实义务行为的类型化,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九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等均是对勤勉义务的具体化规定。《证券法》第八十二条、《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也属于勤勉义务的具体类型。
(二)形式董事的责任体系也存在三重划分
新《公司法》同步规定了违反形式董事义务的法律后果,即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针对第一层守法义务,相应法律责任规定在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条、第一百九十一条,分别是董事对公司的赔偿责任、对股东的赔偿责任和对他人的赔偿责任。
针对第二层忠实勤勉义务,新《公司法》未直接规定相应法律责任。若其他法律对此有规定,如《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证券公司董事勤勉责任)、《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董事破产责任),可予直接援引。若无其他法律规定,则应援引新《公司法》关于违反第一层守法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
针对第三层类型化的忠实勤勉义务,若新《公司法》规定了相应法律责任,则直接适用该规定。比如,第五十一条第二款关于董事违反催缴出资义务赔偿责任的规定,第一百八十六条关于董事违反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义务后归入权的规定。若新《公司法》未直接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则可援引新《公司法》关于违反第一层守法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
事实董事义务责任的具体内容源于对形式董事义务责任体系的准用
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适用前两款(关于形式董事忠实勤勉义务)规定”,因此,事实董事的义务责任内容需要准用形式董事义务责任体系的规则。
(一)对“执行公司事务”的解释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
根据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规定,认定事实董事需要满足“不担任公司董事”和“实际执行公司事务”两个要件,重点是对后一要件“执行公司事务”的认定。
从正面来看,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下简称双控人)执行了形式董事职权范围内的事务。从条文“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措词来看,双控人执行的应当是形式董事可以执行并且应当由形式董事执行的公司事务。新《公司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二十条集中规定了董事会的十项职权,双控人未担任形式董事,但实际实施了形式董事职权范围内的行为,可认定为事实董事。
从反面来看,并非行使了形式董事职权就一律认定为事实董事。认定双控人实际行使董事职权,需要全面考量相关因素:一是行使职权的名义和其他主体对其身份的认知。若行为人以董事身份行事,行为相对人有合理理由认为其为董事,则可考虑认定其为事实董事。二是实际行使董事职权的性质。行为人行使的职权是否为董事会的重要职权,比如代表公司进行投资谈判、讨论决定分红等。若仅按新《公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制作会议记录、按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转交临时提案,则不能据此认定为事实董事。三是实际行使董事职权的程度。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参与董事会重大决策,是否在董事会中发挥相当作用,职权行使是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等。
(二)事实董事准用形式董事制度时需对“适用前两款规定”的内容作扩张解释
依据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事实董事准用前两款关于形式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规定,即在前文梳理的董事义务三层体系中,似只准用第二层关于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规定。
其一,应扩张解释为亦准用第一层和第三层董事义务。前述董事义务体系中,第二层义务是第一层义务的具体化,第三层义务又是第二层义务的再具体化,事实董事准用第二层义务当然隐含着准用第三层义务。比如,新《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二条关于董事为清算义务人的规定,是第三层类型化的董事勤勉义务,应准用于事实董事。在无第二层、第三层义务规定时,亦可考虑准用第一层义务的规定。
其二,应扩张解释为也准用形式董事相应的责任体系。一项完整的法律规范包括权利、义务、责任三个部分,让有董事之权的双控人承担董事义务责任,符合新《公司法》关于董事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价值追求。第一百八十条第三款虽仅提及事实董事准用前两款关于董事忠实勤勉义务的规定,但也应准用形式董事责任的相关规定。
影子董事仅就其指示行为与被指示人承担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指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事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行为的,与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认定为影子董事的核心是双控人实施了损害公司或者股东利益的“指示”行为,相应的后果是与被指示的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一)应从三个层面认定双控人是否存在不当“指示”行为
第一层,“指示”说明双控人的行为具有间接性。其在幕后操纵形式董事或事实董事,其有明确授意,但不直接参与执行董事职责。“指示”可以作为的方式,如明示的授意、指令、指使、指导、指挥,也可以不作为的方式,如消极的隐瞒、默许等。该“指示”不需要影响到过半数董事,只要双控人的指示行为与公司或股东权益受损害的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即可。
第二层,判断是否为“指示”,需要考虑是否超越职权范围、履行相应程序。若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律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要求,指示另一董事从事某违法违规行为,即使该行为损害了公司或股东利益,也不能依据该条规定追究指示者的连带责任。若超越其职权或未满足相应的程序要求,则可能构成“指示”。对于“指示”的认定,要追求实质标准,可根据在案证据,结合日常生活和公司治理的一般逻辑和经验进行认定。
第三层,不单独要求“利用影响力”要件。从英国、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司法律规定来看,认定影子董事均隐含着指示者要利用自身影响力,指示具有一定强制性。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将影子董事的主体限定在双控人范围内,已说明“指示”包含了利用影响力,无需再加上“利用影响力”的要件。
(二)影子董事的责任以被指示人承担赔偿责任为前提
形式董事违反三层义务,从事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形式董事的行为系按照双控人的指示所从事的,双控人当然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背后的原理是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即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新《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是按照侵权法的思路,通过对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审查,来认定影子董事的连带责任,故是一案一议式的,双控人是就自己的某项指示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对公司负有形式董事所负有的权利义务责任。
(作者单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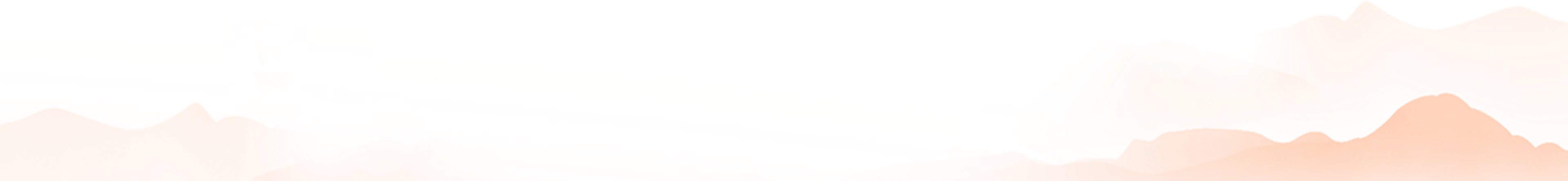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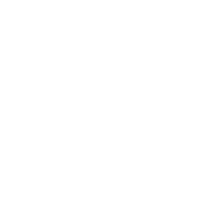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