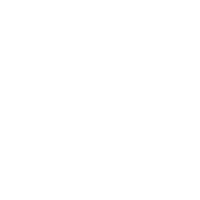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 记者 徐荔
“释放”是刑罚执行的最后一道程序,也是犯人重新获取自由的门槛。
在租界及民国时期,提篮桥监狱对犯人的刑满释放有不同的操作程序。而那时,也有工作人员擅自更改犯人资料,使得犯人提前释放,但好在有专门的工作制度,让这一行为曝光……
释放前的准备
1920-1933年5月间,提篮桥监狱主要有四幢监楼关押犯人,其中AB监又称东监(1933年5月拆除),CD监又称西监(1933年5月拆除),FG监又称南监(后称3号监),H I监又称北监(后称4号监)。当时这四幢监楼的关押犯人有所区别:东监、西监除了主要关押长刑期的犯人外,还有新收与出狱的功能,新犯人入狱的第一夜必须关押在东监,老犯人刑满释放前一天必须关押在西监。
1935年以后,提篮桥监狱扩建部分监楼,添建完成并启用,形成占地60.4亩的规模。对犯人刑满释放的各项手续趋于完善,犯人服刑凡刑期届满者,至少于释放前三日为独居监禁并停止作业。监狱发还犯人入监时由其保管的物品,监狱还规定对被释放者无归乡旅费及衣类得酌情给之,但实际上往往难以落实,几乎是一纸空文。对患重病者及传染病者释放时,则事先通知其家属或亲族。刑满犯人于刑期终结的次日释放。
1946年前后,提篮桥监狱犯人释放时,大致经过如下程序:
(1)由总务科负责登“出监簿”,通知教化、卫生、作业、警卫课及保管股。
(2)停止作业,分房集训。
(3)作业课清算犯人赏予金,交付保管股。
(4)保管股清算保管财物交付本人。
(5)卫生课施行健康诊断。
(6)教化课施行出监教诲。
(7)让被释放人员填写出监感想录。
(8)总务科施行出监手续,核对指纹,填写出监证,通知各层门卫放行。
(9)释放出监。犯人填写的“出监感想录”,列有五个要点:在监中所特觉痛苦或愉快之事;对于官吏之管理上以为不当或适当之事;于囚人间暗中所见或所闻之事;听教诲而有所感,或曾读何书而有所感之事;在监中自觉之事,出监后预想实行之事。当时在押犯人中文盲较多,真正能填写“出监感想录”者为极少数。此办法实际上也徒有虚名,没有真正实施。
释放的手续
提篮桥监狱启用初期,犯人释放送交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由总巡捕房办理犯人出狱手续。后来,提篮桥犯人刑满出狱,不需通过巡捕房,由监狱直接办理出狱手续。监狱犯人出狱前几天,由监狱负责采录犯人指纹,送总巡捕房指纹室(手印间)交验指纹。
如果刑释犯人指纹和姓名、番号、案由等符合,由指纹室加盖印章,监狱凭此材料放人;如果指纹与犯人姓名、番号等不符,监狱严禁释放,以防止犯人间冒名顶替,或管理人员故意“调包”,李代桃僵。
犯人释放时脱去囚服,由监狱负责发还犯人入监时所穿的衣服和保管的物品。
20世纪30年代初期,监狱释放犯人,由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签发释放令发往监狱,命令监狱在指定日期释放某犯人。
释放令有两个部分组成:一是被释放犯人的姓名、人数、罪行、法院案号、警署名称、判决和释放理由、法院印章和签发法官姓名;二是在犯人释放后由监狱管理人员填写释放日期、时间,然后送回法院。
释放的地点
提篮桥监狱启用初期,犯人刑满释放的地点在福州路的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由总巡捕房办理犯人出狱手续。例如,章太炎曾于1903年因《苏报》案被会审公廨判处监禁三年,关押于提篮桥监狱。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由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办理出狱手续,经过核对指纹,查验身份后,在福州路上释放。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在当时也属重要的社会新闻。时在日本的孙中山特地派了两位同盟会成员从日本抵达上海专程迎接。当日上午10时,章太炎跨出福州路巡捕房的大门时,等候已久的蔡元培、叶瀚、蒋维乔等人迎上前相拥相握。被人扶上马车,直驶吴淞口,当晚离沪东渡日本。
后来,提篮桥监狱犯人刑满释放的地点有所变动,犯人释放时,由监狱看守把他们移押到北浙江路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由会审公廨出面办理刑满释放手续。
1927年,会审公廨被中国政府收回,改为上海临时法院后,这一做法被废止。
20世纪30年代,提篮桥释放犯人时,在办毕出狱手续后,不让犯人直接走出监狱的二大门、一大门,而是把他们押上囚车或有棚的大卡车,把他们带出监狱,故意拐了几个弯道后,把车辆停靠在监狱不远处的马路边,才把他们释放回家。
有时候,也把部分犯人的释放地点安排在公共租界工部局或福州总巡捕房。例如,革命志士任富定1935年6月26日在上海巡捕房被逮捕,后被判处两年半,7月囚禁提篮桥监狱,1937年12月25日刑满,在监狱办完相关手续,乘上囚车后被送到福州路中央捕房门前释放。
后来,随着提篮桥监狱犯人增多,出狱犯人数量也增多,犯人刑满释放时,才让他们直接走出监狱。
统计人数发现猫腻
1949年前,提篮桥监狱曾设“三科两所”,即总务科、警卫科、作业科、教诲所和卫生所。其中,总务科的管理范围较多,管理监狱犯人的收监、减刑、释放、物品保管、统计、名籍、文书;职员看守的接收、辞退、会计、财务等,所以按职能而言,总务科又称“第一科”。
当时,犯人的各种卡片资料是监狱的机要材料,平时各类档案和卡片资料只有总务科的工作人员才能看到。监狱制度规定,各科室工作人员不准互相串门、交谈,也不准随意到各监楼;看守人员同样不准随意进入监狱各科室。
那时,提篮桥犯人进出量相当大,在押犯人最高达七八千人,其中短刑犯占了较大比例。为了确保监管安全,做到及时收押、准时释放,监狱里形成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管理措施,收押和释放时注重犯人指纹的验证。
1943年12月,当时在提篮桥监狱工作的柏其林在做当年犯人年报,核对监狱押犯统计数时,突然发现监狱两套卡片资料上有误差,留底的一张多了一人,上报的一张少了一人。如果从数学计算上讲,其误差率在几千分之一,似乎微乎其微。如果从物资管理部门来说,也许是物品的“自然损耗”,但是从监狱管理工作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犯人人账一丝一毫都不能出错。为此,柏其林又进一步地探究,发现大办公室一套资料上显示某犯人已经刑满释放,但是小办公室资料上却反映该犯刑期未满,仍在狱内服刑。这种情况监狱过去没有出现过。
柏其林拿着两套卡片资料,又做了一次核对,经仔细辨认发现,放在大办公室里的一套资料上,这个犯人的入监、出监日期有被人涂改的痕迹,与小办公室的资料相比,该犯人的入监、出监日期明显地提前了。柏其林又到监狱档案室找来法院的判决书,果然该犯人资料被人做了手脚。这个犯人是被人通过“合法手段”堂而皇之地提前释放,走出了监狱大门。
“书记官”私放犯人
柏其林马上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了当时的典狱长邢源堂。
邢源堂,江苏江阴人,长期在司法监狱系统工作,他是提篮桥监狱历史上第一个出任典狱长的中国人。1943年8月,邢源堂从浙江第一监狱典狱长任上调到上海。
对这起因私改刑期被提前释放的事情,邢源堂等经过排摸,疑点集中在总务科的另一名书记官厉某身上。在确凿的事实面前,厉某最终交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厉某当时是分管监狱犯人出入监工作的人员之一,家住提篮桥监狱周围,平时交际的人员较广,朋友较多。他有文化,在监狱工作多年,对各类狱政业务比较熟悉。
有一次,厉某受朋友之请托,并拿了几千元的好处费,私自更改了那位朋友所托的在押犯人的入监和出监日期。因为当时监狱总务科备有多套犯人卡片,有一套是按犯人的出监日期为序,如某年某月1日释放的人放一沓,某月2日释放的人放另一沓,其余类推。由于厉某私自更改了那个犯人的入监和出监日期,而且一切干得十分“干净利落”。这个被做过“手脚”的犯人,和正常刑满释放的犯人一起按捺指纹,按照正常程序出狱,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厉某利用职务之便,更改了监狱日常使用的一套犯人卡片资料。但是厉某不知道总务科内还有另一套存档的犯人卡片资料,由柏其林管理,平时又锁在铁柜里。而且监狱规定,他们两人的工作不准互相通气。所以,到了年底做年度统计报表核对人账时使得这起舞弊枉法案曝光。后来,厉某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
(整理自《上海监狱的时光踪迹》徐家俊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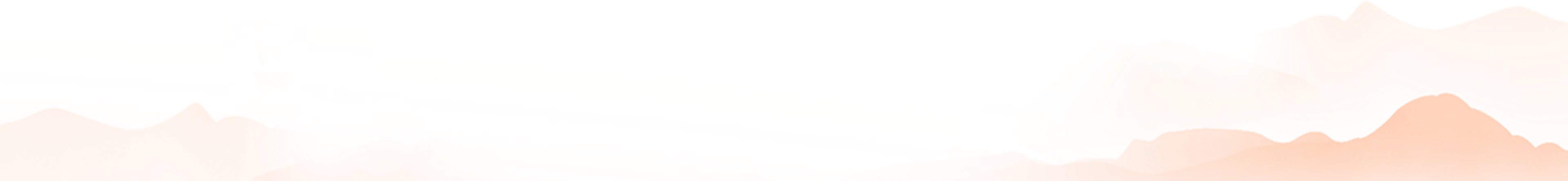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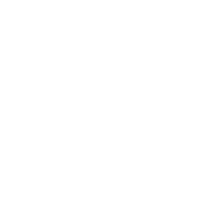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