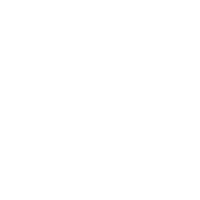金泽刚
近日,黑龙江省林区公安局迎春分局破获一起非法狩猎案,三人在车内使用无人机、箭矢等非法狩猎两头野猪,目前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此类“无人机狩猎”案件其实已并非个例。科技创新总是领先于立法发展,法律如何及时应对,有效规制技术滥用,填补监管真空,守护公共安全与生态平衡,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无人机搭载金属箭矢狩猎的行为,以非法狩猎追究刑责的法理基础在于,该行为已经符合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虽然野猪已被移出“三有”动物名录,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捕杀。根据《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必须持有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和方法进行猎捕。《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狩猎罪。同时,若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以外的其他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情节严重的,还可构成“非法狩猎陆生野生动物罪”。本案中,无人机狩猎者的非法狩猎行为可能涉嫌上述两个罪名。
不仅如此,无人机在野外升空并投射具有杀伤力的箭矢,也蕴含着巨大且不可控的公共安全风险。一旦失控、操作失误或受到干扰,就可能伤及不特定的行人、车辆或公共设施。这种在公共场所实施的、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或重大财产安全的行为,也可能被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或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
由上述分析可知,刑法本身并未对无人机的使用作出具体规定,而非法狩猎罪作为行政犯,其罪名成立以违反狩猎或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等行政法规为前提。只要依据现有相关行政法规能够确认无人机非法狩猎行为的违法性,刑法即可覆盖相关违法犯罪行为。
但此类案件明显暴露出无人机监管链条存在系统性漏洞。在电商平台,搜索“无人机空投”“狩猎箭矢”等关键词,可轻易找到相关商品,有商家甚至提供“从入门到精通”的全套改装教程,指导买家如何增强箭头穿透力、提升无人机载重量。相关工具获取门槛很低,不需要任何资质条件,最低仅需几十元即可配齐全套空投金属箭等利器,如何规制这种“帮助犯罪预备”的风险行为成为当务之急。
从立法规范来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主要规制飞行活动本身,而对无人机挂载何物、用作何用缺乏有效而具体的约束。这就形成了监管的“半真空状态”,即“飞行需要报备,但改装无人监管;设备需要登记,但用途无人问津”。对此,部分地区已开始立法探索,如山东省和武汉市的无人机安全管理规定都着重于维护公共安全秩序,明确禁止利用无人机实施“危及他人生命健康”或“投放危险物品”等行为,湖南省浏阳市则在禁猎通告中明确将“使用无人机等飞行器辅助投射标枪或箭支装具”列为禁猎工具。
为有效规制无人机狩猎行为,不妨考虑从以下三个层面系统完善监管制度。首先,通过修订《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明确将“使用无人机等智能设备进行攻击性狩猎”列为法律禁止的狩猎工具和方法。此举可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空间。参考浏阳市等地的经验,将此类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现执法标准的规范统一。同时,应严格落实空域管理规定,特别是管制空域的飞行审批要求。对于未经批准的飞行行为,应依据《条例》予以处罚,情节严重的可没收无人机。
其次,加强对无人机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管,建立关键配件编码管理制度。压实电商平台责任,要求其建立用于非法狩猎的无人机改装件负面商品清单,主动筛查下架,并对相关销售行为进行严格审核,匹配相应的处罚条款规定。
最后,健全社会协同治理机制。无人机狩猎涉及空域管理、野生动物保护、社会治安等多个领域,需建立公安、民航、空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提升处置效率。网络监管部门与短视频平台需加强对猎杀动物类内容的审核,防止形成不良模仿效应。通过普法与科普,引导公众正确认识野生动物科学管理的重要性,认清无人机狩猎的违法本质与潜在社会危害。
无人机狩猎案看似是针对动物的违法行为,实则是技术进步向法律体系发出的新型拷问。在科技快速迭代的今天,法律必须保持足够的敏锐度和前瞻性,及时跟进纠偏。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技术飞跃真正服务于人类文明进步,而非成为破坏生态、威胁公共安全的推手。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犯罪学学会常务理事)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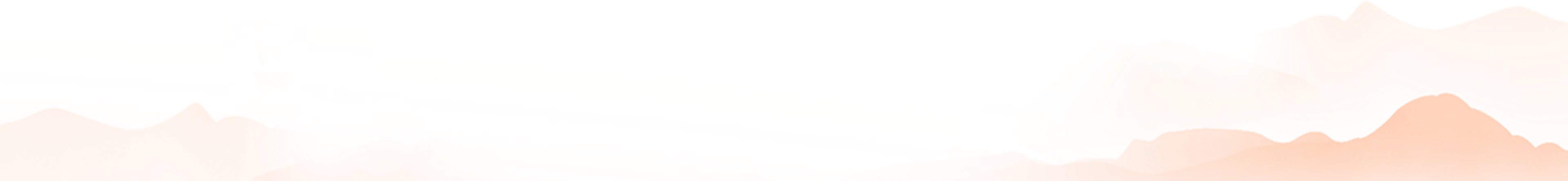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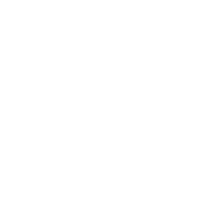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