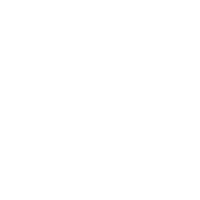□荆山客
运气这件事说起来好像有点迷信色彩,可它确实是存在的。对一个人来说,运气是好是坏还要综合他的整个人生状况来看。打麻将输了钱会怪自己的手气不好,这“手气”就是运气。假如赢了呢,那运气当然是好的。这是一时一事,小打小闹,不足为训,对人生也没有意义。一个人有了足够的阅历之后,他会深信运气之于人的一生往往有着不能小觑的作用,到后来甚至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人生命运,好坏皆是注定,逃也逃不掉的。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叫《舒婷的赌气和运气》,说到诗人舒婷运气好。1977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海风习习。在夜来香弥漫的美丽鼓浪屿,舒婷陪着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散步。闲聊到女性,蔡先生说:“有的女性漂亮,但没有头脑;有的女性有头脑,但又不漂亮;还有些女性既漂亮又有才华,但是不温柔。”舒婷听了很不爽,当晚回家即赌气写成了《橡树》,据说夜里还“发着高烧”。第二天她便把这一纸诗稿交给了蔡先生。接下来就全是运气了。蔡先生去北京的时候把这首诗推荐给诗人艾青。久不见好诗的艾青喜欢至极,认真地抄在本子上,并建议把原题《橡树》加个“致”字,真可谓一字之师。那时候艾青还没平反,赋闲在家,北岛时常陪着他。于是北岛也看见了,就拿去发在他和芒克主编的油印诗刊《今天》上,并张贴到北京的西单墙。差不多两年时间,又被时任《诗刊》编辑部主任的诗人邵燕祥先生看到,拿去发表在1979年《诗刊》4月号上,于是舒婷一夜成名。少了蔡其矫,舒婷这首赌气的诗就不一定写得出;少了其他那位诗人的环节,这首诗就不一定能面世。舒婷的例子说明,运气确实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诗人要有真才华。
同样好运气,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先生当年也是遇上的,可后来这运气仿佛转化为晦气,变得十分糟糕。
人的阅读趣味确实是有差别的,这差别就是来自关注点兴趣点的不同。比如说“七月派”重要诗人绿原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诗,而是因为他是“胡风反党集团”的重要分子(当然现在是笑谈了,都已经平反),他当年因为被打入胡风反党集团是很吃了些苦头的。绿原先生本姓刘,早年我读过他的一篇有小传性质的文章叫《我的这个名字》,讲述他笔名的由来,其中有个细节印象深刻。
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初,绿原先生还是个四处打工热爱文艺的小青年。机缘凑巧,他认识了诗人邹荻帆和冀禤。因为都是年轻人,又都是湖北老乡,很谈得来,大家处得十分融洽。邹先生就劝他考大学。可他高中都没毕业就四处闯,是没资格考大学的。战时虽然很混乱,但大学的招生还是有板有眼十分正规。冀禤先生说他有办法,就给了绿原一个多年失去联系的同学某师范学校的毕业证。这毕业证上盖了钢印的照片,因为年久受潮已经一片灰白模糊不清,证件的主人是个周姓的名字。绿原先生就用它去报考,居然蒙混过关,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外文系。四年大学生活,绿原先生就一直用周姓的名字读下来。虽然也是冒名顶替,这和近年来各地不断揭露出来的冒名顶替别人上大学不同,绿原先生毕竟是以自己的真实成绩考取的,战时的周姓学生不知身在何处,即使绿原不用他的毕业证,那个毕业证也是一张废纸了。
1944年大学毕业,美国和国民政府合作建立“中美合作所”,因为他读的是外文系,校方按照军方的要求分配他去中美合作所。那时绿原已经小有诗名,而且也认识胡风,他就写信征求胡风先生意见,去还是不去?胡风先生不了解这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告诉他要谨慎些不要去。结果1955年因为这封信,胡风的罪名又加一条是“勾结国民党”,绿原的罪名是“美蒋特务”。
福兮祸所倚,谁说得清呢?我就想,如果当初他不认识诗人邹荻帆和冀禤,或者没那个师范学校的毕业证,绿原先生考不上大学,那么他的命运会如何呢?想了半天的结论是:那就没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和翻译家绿原先生了。就像绿原先生后来的感叹:“本来,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叫什么不叫什么,无可无不可。我们叫它玫瑰的那个东西,叫其它任何名字不也照样香吗?予岂好名哉,予不得已也!”
SourcePh" style="display:n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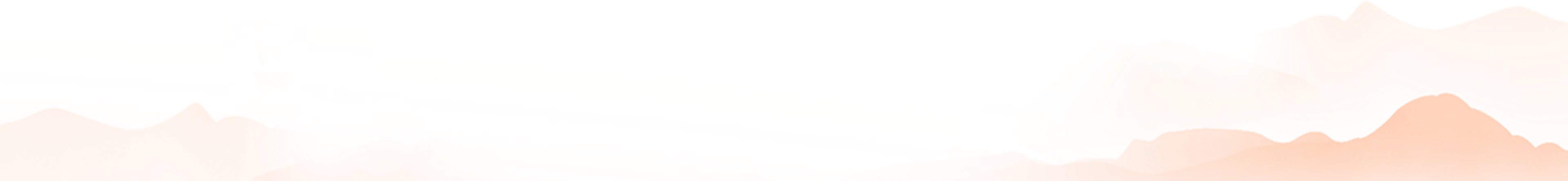



 首页
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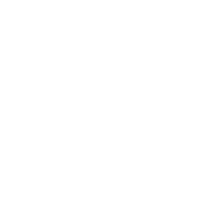
 放大
放大 上一版
上一版